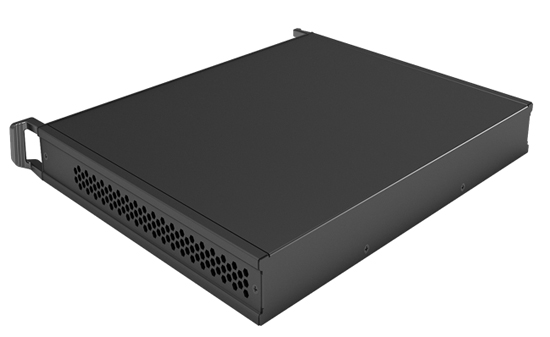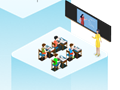為什么要“先識字后學拼音”
http://www.hai34.com2025年11月17日 14:57教育裝備網
從2017年開始投入使用的統編小學語文一年級教材,采用“先識字后學拼音”的教學順序,在“漢語拼音”單元之前,先安排一個“識字”單元。這一編排方式,在當時引起了熱烈的討論。經過8年的教學實踐檢驗,這一做法取得了很好的教學效果。當然,社會上也有個別不同聲音,所以有必要對“先識字后學拼音”教學順序的學理依據與實踐基礎再作簡要分析。
從漢字的性質看
漢字作為世界古老文字中唯一持續使用至今的表意文字系統,其形、音、義之間的關系與拼音文字存在本質區別。漢字是記錄漢語的工具,漢字的形音義三要素中,音和義來源于漢語中的詞(詞是音義的結合體),只有形才是漢字的本體要素。漢字在記錄漢語中詞的時候,是以自身的形與詞的意義建立直接聯系的,而不像拼音文字那樣是以形與詞的讀音建立直接聯系。例如,象形字“日”“月”就是勾畫太陽和月亮的輪廓;指事字“本”“末”就是用指事符號標示所指的具體對象;會意字“休”用“人”和“木”組合表示人靠在樹上休息,“明”用“日”和“月”組合表示明亮。這種形義關系使得漢字能夠不依賴語音直接關聯意義,形成了漢字特有的認知方式。特別是在前置“識字”單元中,專門為“日、月、山、川、水、火、田、禾”等象形字配上了圖畫和古文字形,讓學生建立起從圖畫到古文字再到楷書漢字的聯系,感知漢字象形性的特點,領悟漢字的造字原理,這對激發學生的識字興趣、從一開始就確立漢字形義關聯的意識是很有幫助的。
漢字構形具有很強的系統性,其中90%以上的現代漢字是形聲字。形聲字由表義的形旁和表音的聲旁組成,這種結構使得漢字學習不是孤立的個體記憶,而是可以將具有相同形旁和聲旁的字類聚在一起,進行集中識字。如“木”旁的字多與樹木有關(樹、松、柏、梅),“氵”(水)旁的字多與水相關(江、河、湖、海)。形聲字的形旁和聲旁常常由獨體字充當,先學習一些構字能力強的基礎漢字(如“水”“木”),可以為后續學習合體字奠定基礎,符合由簡到繁的認知規律。正如清代文字學家王筠在《教童子法》中所說:“蒙養之時,識字為先,不必遽讀書。先取象形、指事之純體教之。”這一觀點體現了古人對漢字系統和認知規律的深刻把握。教材前置“識字”單元安排30多個漢字,其中多數為“人、口、耳、目”之類的獨體字,也有“地、你、他、坐”等合體字,就是為了讓學生初步感知漢字的形體特點和構形規律,為今后的語文學習邁出堅實的第一步。
從漢語拼音的定位看
1958年1月10日,周恩來總理在全國政協舉行的報告會上作了《當前文字改革的任務》的報告,明確說明了漢語拼音方案的用處,“是用來為漢字注音和推廣普通話的,它并不是用來代替漢字的拼音文字”。1958年2月11日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《關于漢語拼音方案的決議》,進一步明確其功能為“幫助學習漢字和推廣普通話的工具”,而非獨立文字系統。這一定位決定了漢語拼音在識字教學中的輔助地位。
毋庸諱言,漢語拼音方案在漢語學習中確實發揮了重要作用。拼音既是注音工具,也是正音工具,很好地彌補了漢字字形與讀音關聯不夠密切、形聲字聲旁不能精確標音的不足,可以精準標音,幫助人們統一發音,更好地學習普通話;拼音還是識字的橋梁,在學生積累一定識字量后,可以通過拼音自主認讀生字,提高識字的速度和效度,擴大識字量。但無論拼音的作用何等重要,它也絕不可能與漢字等量齊觀,更不可能取代漢字。
中國古代原來并沒有拼音字母,常用的注音方式是直音法和反切法,前者是用同音字來給漢字注音,后者是用兩個漢字來拼合一個字的讀音,這兩種方法都是漢字內部的注音策略。直到明朝末年,才開始引進外來的字母為漢字注音。現行的漢語拼音方案采用的是拉丁字母。可見,無論從其來源還是引進時間來看,漢語拼音對于漢字來說都是外在的東西,不是其本有要素。因此,識字教學的核心目標是漢字,拼音只是輔助漢字學習的工具,不能本末倒置。原來一入學就集中進行拼音教學的模式,學生根本不知道學拼音是干什么用的,誤以為學拼音就是目的,違背了為幫助識字而學的初衷。語文教材對拼音教學進行了應用導向的改革,明確了拼音的工具性定位,強調拼音與已學漢字的結合,注重拼音在實際場景中的應用,增加實用功能練習,使拼音教學更加聚焦其工具本質,提高了學習效率和實用性。
從古今的實踐經驗看
中國古代漢字教學有著悠久的歷史和豐富的經驗,特別是以“三百千”(《三字經》《百家姓》《千字文》)為代表的古代蒙學教材,集中體現了古代集中識字、韻語識字、識字與育人相結合的教育智慧。由于直音法、反切法都是用漢字給漢字注音的,傳統蒙學教育必須遵循“識字為先”的基本原則。學生只有積累了一定數量的漢字,對漢字結構有了基本認識,對反切的原理和方法才能夠理解。此時再去學習反切法,既具有明確的目的性,也具有可行性。這種教學模式一直延續了兩千余年,形成了植根于中華教育傳統的歷史經驗。
傳統蒙學教育注重漢字的形象性,這也正符合兒童認知發展的規律。現代認知科學研究表明,兒童認知發展遵循從具象到抽象的基本規律,一年級的兒童多數為6—7歲,正處在以形象思維為主的階段。漢字具有形象性、可解釋性,能夠通過圖形聯想幫助記憶。而拼音符號是抽象的語音代碼,與意義沒有直接聯系,需要更高的抽象思維能力,而且拼音字母是舶來品,相對于常見的漢字來說,孩子們普遍會覺得外形陌生,存在文化差異感,不利于引發學習的興趣,因此不宜先于漢字學習。
其實,關于“先識字后學拼音”的實踐探索早就開始了。在本世紀初,有些地區就曾采用過這樣的教學方式,先從學習漢字入手,經過幾個單元的識字教學后,在學生積累一定數量漢字的基礎上,再開始進行拼音教學,取得了一定的實踐經驗。2017年開始,全國統一使用統編語文教材,借鑒此前的相關經驗,采取了“先識字后學拼音”的編排方式。剛開始,有些教師和家長對這種改變感到不適應,但隨著新方法的優勢在實際教學效果中逐漸顯現,以及大家對其學理依據認識的深化,廣大教師和家長對這一改革舉措給予高度認可,新的教學理念逐漸深入人心。
應該說,“先識字后學拼音”的教學模式不是簡單的教學順序調整,而是對漢字教學和語文教育規律的理性回歸,是對古代教育智慧和文化傳統的繼承與發展,值得在實踐中不斷完善和推廣。
(作者系北京師范大學中國文字整理與規范研究中心主任)
作者:王立軍
責任編輯:董曉娟
本文鏈接:TOP↑

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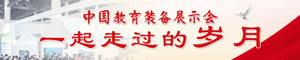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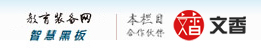

 首頁
首頁